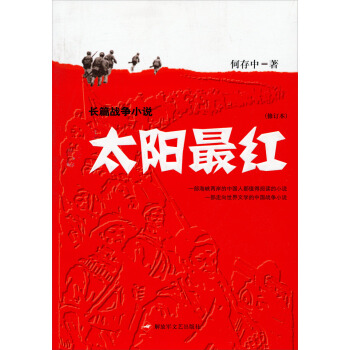
太阳最红
作者:何存中
字数:225807
阅读:107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以大别山地区“黄麻起义”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思考革命过程中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破坏与重建的长篇小说。小说再现了红四方军早期十年组建过程中,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史和中华民族精神史。小说以外甥王幼勇的一家兄弟姐妹与亲舅舅傅立松的一家斗争为主线,展现了爱恨情仇、可歌可泣、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故事。
分类: 军事战争
0个粉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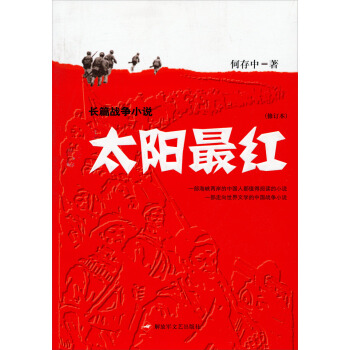
作者:何存中
字数:225807
阅读:107
这是一部以大别山地区“黄麻起义”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思考革命过程中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破坏与重建的长篇小说。小说再现了红四方军早期十年组建过程中,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史和中华民族精神史。小说以外甥王幼勇的一家兄弟姐妹与亲舅舅傅立松的一家斗争为主线,展现了爱恨情仇、可歌可泣、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故事。
分类: 军事战争
评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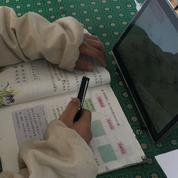
更多评论 >古田四郎 2017-07-10 16:35:10
《太阳最红》是第一部以大别山地区黄麻起义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再现了红四方军早期十年组建过程中,艰苦卓绝血雨腥风的革命奋斗史。那是一场革命的土地上爆发的土地的革命。 政治与经济是一个大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如同车之两轮。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寻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前,一直在依赖中幼稚地生存与发展,处于革命的低级阶段。经过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和经验的积累,中国革命终于走出低谷,向高级阶段迈进。而这个过程,自然充满着残酷的流血和牺牲,写下了人间的大悲剧。《太阳最红》给中国战争小说贡献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它第一次挖掘并完整精彩地呈现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第一部把经济问题作为战争主要问题来考察和进行艺术思考的作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队伍同样民以食为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的后勤保障如何展开,这是关系革命斗争成败的关键。 小说中,王幼勇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攻打红安县城后,三万衣衫褴褛的苦难兄弟因为没有粮食准备,饿着肚子喝干举水河河水的场面撼人心魄。在那血雨腥风贫穷落后的年代,衣食住行尤其是吃饭的问题或许比革命本身更加迫切。因为革命队伍的主体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没有土地的穷人,他们之所以参加革命就是要解决有饭吃、有衣穿的温饱问题,这是土地的命运也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命运。作品主角王幼勇作为一个时代的新青年和知识分子,在革命的洗礼中成功完成了党赋予他着手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任,建设银行、发行货币。而为了经济建设,作为苏区苏维埃银行行长的王幼勇与舅舅傅立松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地较量,比枪林弹雨中战场上的生死较量更加惊心动魄。作家何存中在这方面的情节设置和细节描写,凸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因此《太阳最红》在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方面的新开拓,无疑是中国战争文学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收获。 伦理与道德是人类的永恒话题,也是文学始终绕不开的情结。《太阳最红》典型地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集中在一个家族的内部矛盾中。具体的说就是姐姐和弟弟(傅大脚和傅立松)、外甥和舅舅(王幼勇兄妹和傅立松)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是扎根在血浓于水的血缘亲情和养育之恩之间,可谓有血有肉,大爱大恨,有情有义、大喜大悲。而这个家族的矛盾,如果我们把它还原到历史的现场,就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矛盾,而是在革命的洪流之中突出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回顾历史,其实中国革命的成功绝非靠《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这样的英雄,而更多的是靠一大批有文化、有才气的革命者在血与火中煅铸了成败,并成功领导组织了人民。而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建议何存中先生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正面强化,以更清楚地说明革命的合理性或者合法性。于是在作品的第六十三节傅立松活埋王幼勇之时的对话中加入了这样的一段——“王幼勇说,你不用在我面前忏悔。你对不起的只是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傅立松说,我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现在只有你让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王幼勇说,你伪善,假革命。中山先生说,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你对不起的是天下百姓。”毫无疑问,“平均地权”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和土地革命的核心!傅立松因为没有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就当然的成为革命的对象和敌人。 不破不立。改变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没有流血牺牲是难以想像的。革命的艰巨复杂和战争的悲壮惨烈,不是英雄的传奇。《太阳最红》既改变了《林海雪原》《红日》《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红色经典长篇战争小说的叙事模式,也改变了《亮剑》《历史的天空》等新世纪战争文学的宏大叙事和英雄传奇的打造,而是把眼光投入民间,忠于历史、忠于生活、忠于信仰和理想,挖掘革命历史沙漏中的金子——为革命牺牲的人民和人民的牺牲。 因此,《太阳最红》创作的贡献,还在于它没有模式化的表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没有复制历史,更没有复制文学,而是百分百地原创。在我看来,原创就是不可复制。创作中,何存中没有简单化地回避牺牲和痛苦的悲剧,没有戏剧化地歌颂战争的胜利和成功,而是用积极的向前看的眼光,尊重那一个时代那一片土地和那一段历史以及历史洪流中的人和事,让众多鲜活的人物交织在一起,在血与火、生与死、道与义等多重生命价值中构成厚重苍茫的人生主题,让人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生命的意义进行积极的思考,举重若轻地写出了革命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